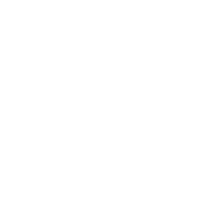十岁那年暑假,妹妹失踪了,消失在给父母送饭的路上,十五年后,我做了警察,一遍遍重走她当年走的路,结果拼凑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
发布日期:2025-10-08 10:19 点击次数:130

十岁那年暑假,我妹妹突然消失了。
消失在给父母送饭的路上。
周围没有摄像头,也没人见过她的踪影。
因为饭本该是我去送的,从哪以后妈妈一句话都没对我说。
时光过去十五年,我成了警察,一次又一次地走着妹妹当年走过的路。
那些尘封的记忆渐渐浮现,点点滴滴拼凑出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
……
2009年8月10日。
就是妹妹失踪的那天。
那时我们一家还住在城郊结合部一处破旧的院子里。
爸爸在附近的化工厂当工人,妈妈开着公路边的小杂货铺,生意红火得很。
夏天中午,很多人都会来买冰棍雪糕,爸爸下班后经常帮忙,顾不上吃饭。
所以整个暑假几乎是我在做全家的饭。
厨房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旧风扇。
水开后厨房里的热气腾腾,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我做饭时汗水湿透了全身。
那天特别热,饭做完时我有点中暑。
家里没人帮忙,奶奶虽然住隔壁,但性子刻薄,不但不帮忙,还总爱说难听话,我不敢去麻烦她。
我洗了把脸,忍着头晕,给妹妹盛了一碗冷面条,让她先吃。
然后又装好爸妈的饭盒,放进篮子里。
“姐,你躺着吹会儿风扇,我今天送饭吧,路我熟。”
妹妹吃了几口面条,小声说。
“剩下的我回来再吃。”
从我们家到杂货铺只有条十分钟的路,路也不偏僻。
平时我都带着她走这条路,无数次了。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你真的行吗?”
我半躺着,额头上搭着湿毛巾,问她。
“没事,放心吧姐,就这点路,马上回来。”
她不答话,拎起篮子就往外走。
妹妹是个常年病弱的孩子,身子瘦小,一用力肩膀上的骨头就突出,那个小小的背影,看得人心酸。
临走的时候,她还朝我挥了挥手:“我马上就回来,我的面条,姐姐可不能偷吃哦!”
“放心吧,我才不吃呢!”
我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让她走。
可是,她却再也没回来。
“你说,要是那时候我说我会偷吃她的面条,她心里惦记着,是不是就会回来了?”
2024年1月9日,我正式进入市公安局,成了一名见习警员。
八个月后,我跟师父老余聊起了这件折磨我十五年的悬案。
“什么时候发现的?”
老余问。
我揉了揉眼睛,回忆说:“差不多下午两点多吧,她走后,我刚吃了两口面条,就睡着了。结果是被爸的一巴掌给拍醒的。”
尽管已经过去很久,那一幕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刚睁开眼,迎面就是爸那张怒气冲天的脸:“你干嘛不去送饭?想饿死我们啊?”
我一哭:“妹妹早就去送饭了呀!”
话音刚落,我才看到饭桌上还剩下一半的面条,猛地想起妹妹还没回来。
一股寒意顺着脊背直窜上来,眼泪瞬间被恐惧吸干,干巴巴的。
“我们找遍了所有地方。那时候‘天网’还没覆盖这条小路,只有主干道才有监控。全家像无头苍蝇似的疯找。”
“池塘边的竹排捞了三遍,水井里也派人下去查了,都没有她的影子。”
“报警后,警方调了周围监控,连个可疑人都没查到,邻居们,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说没见过她。”
妹妹,就这样消失了。
妈坐地上捶胸顿足,哭得撕心裂肺:“你怎么就那么懒?不去送饭,让她去送饭!”
信基督教的奶奶说,她的主绝不会饶恕一个因为懒惰和自私,害得妹妹失踪的孩子。
爸气得连踢我五六脚,一脚把我踹倒在地。
邻居们弄不清白,也没人敢过来劝,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全都落到我头上。
我像个没有感情的木偶,一滴眼泪都没掉,默默走到妹妹失踪的那个路口,执拗地站了整整三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路,盼着能看到她那小小的身影出现。
可奇迹始终没发生。
从那以后,家里的人都少跟我说话,尤其是妈妈,接下来的十几年,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
到了中学,我开始住校,周末才回家一趟,回来就是拿点钱和换洗衣服,根本不敢多待一会儿。
那些年,我一次又一次地沿着妹妹当时送饭的路走,仔细看着路边的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拼命寻找哪怕一点蛛丝马迹,脑海里反复演绎着无数种可能。
那段时间,真是煎熬。
“你平时午觉一般睡多久?”
老余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一边翻着我带来的卷宗,一边问。
那个案子当年被判定为失踪案,直接搁置了十几年。
“看情况,有时候睡得久,有时候睡得短。但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困,竟然睡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我爸来叫醒我。”
“那你说你当时是中暑,对吧?具体的感受还记得吗?”
我努力回忆着那天中午的情形。
“浑身乏力,特别困,头晕,头重脚轻……”
老余听完,沉默了会儿。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并不是中暑?”
我一下子心头一紧,猛地睁大眼睛盯着他。
“中暑的症状是头晕眼花、耳鸣头痛,四肢没力,还有恶心呕吐,出冷汗……”
“你的症状倒不像中暑,更像是吃了……”
我心里突然一惊,没等他说完,忍不住插嘴:“吃了什么?”
“安眠药,或者含有催眠成分的药。”
老余眼神复杂地说道。
我怎么没想到呢?
安眠药和中暑症状确实很像。
但中暑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恶心呕吐和出冷汗。
可那天,我清清楚楚没出现过这些。
一瞬间,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当年大人们,包括警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偷懒,就怕热才让妹妹去送饭。
我说的每句话,都被当成了推脱责任的借口。
大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找人上,结果居然错过了这么关键的线索。
“师父,你怎么会怀疑我不是中暑呢?”
我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心里终于有了盼头,案子竟然有了突破。
老余一边翻着卷宗,一边慢悠悠地说:“很简单。
听你讲你和妹妹的事情,就知道你们感情深厚。
她还小,自己去送饭,你肯定很担心她。
照理说,你应该一直熬着,等她回来了才睡,但你却睡着了,而且睡得还特别沉。
要不是你爸来叫你,估计你还能睡更长时间。”
“显然,这不正常。”
他说到这儿,眼神里带着几分坚定。
我眼眶湿了,忍不住点头。
这么多年,老余是第一个注意到我和妹妹之间不同寻常感情的人。
当年妹妹失踪后,爸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怎么当老大的?妹妹都不见了,你居然还能睡得着?你怎么不气死你自己?”
那时候,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毫无征兆地睡过去,连自己都恨自己。
没人知道,我有多喜欢妹妹。
更没人懂我们之间的感情远远超过姐妹那点平常的爱。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几乎整天黏在一起,24小时形影不离。
更因为无论多冷多热,我们总是紧紧依靠在一起,一起面对艰难困苦。
父母忙着做生意,经常把我和妹妹丢给奶奶带。
可奶奶信基督,经常去参加教友聚会,把我们丢在家里整整一天不管不顾。
所以,从六岁起,我就学会了自己下厨给妹妹做饭。
哪怕饭煮得糊了,我们也一起吃,煮得香了更是分享。
别的孩子喊妈妈,而我妹妹痛哭时喊的,永远都是“姐姐”。
“那天你出了很多汗,应该喝了不少水。
问题应该就在水里。”
老余指了指我面前的水杯。
我忍不住问:“可是,谁会对一个十岁的小孩下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说出这话时,脑海里浮现的两种可能都让人十分绝望,甚至更加让人绝望。
“你们家有仇人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爸妈做生意一直讲究和气生财,很少跟别人起冲突。
家里唯一一个不对付的人,那天也有不在场的证据。”
正说着,外面突然吵闹起来。
一对夫妇急匆匆地冲进警局,报案找孩子。
“警察同志,我家孩子八岁,有自闭症。孩子爸爸带着他去做康复训练,路上把孩子弄丢了。”
女人焦急得几乎要跪下来,满脸都是祈求。
男人则垂头丧气,语气低沉,可神情里却藏不住一丝轻松。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差不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毕竟,我入职警局还没一年,但类似的案子已经遇到好几回。
大多数都是问题孩子,家里负担不起治疗和康复的费用,或者父母早已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看不到希望,所以选择遗弃孩子,但又怕被人指指点点,就干脆来报警做做样子。
不过,尽管心里有数,我还是详细问了男人事情的经过。
“我们路过滨海公园的时候,孩子看到有人在喂海鸥,怎么拉都拉不走。我只好去买一份喂海鸥的粮食。结果,就这么一转身,孩子就没了。”
孩子是在下午五点多丢的,那时候正是海水涨潮的时候。
他们四处寻找没着落,才赶紧报警,此刻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如果遇到危险,生命可能瞬间就没了。
要是碰上人贩子,这两个小时足够孩子被带到汽车站或者火车站了。
已经太晚了。
不过,警局不可能不管。
老余让我马上发出寻人启事,以孩子失踪地点为中心,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同时,安排一个支队奔赴各大交通枢纽寻找孩子,又联系了两个专业搜救队在海边连夜搜索。
三管齐下,所有能做的措施都已经启动。
剩下的,就看孩子的命运了。
那对夫妻离开时,千恩万谢。
老余看了眼外头漆黑的夜空,说:“这孩子活着的可能性不大了,尸体迟早会被找到。”
我拼命摇头否认:“不会的。我妹妹有严重的哮喘,也不是没可能……但我们家从来没嫌弃过她。她丢了以后,我成了家里最大的罪人,妈这十几年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看了我一眼,敲了敲案卷说:“那你奶奶呢?她对你们姐妹俩怎么样?”
我一惊:“你怀疑是我奶奶?”
确实,除了爸妈和奶奶,没人能往我水里下安眠药。
“也不是怀疑,只是排除可能性,分析案情而已。”
“说实话,这不太好说。但那天有人作证,她在邻居家做礼拜,一时间也算有不在场证明。”
老余沉默了下,又问:“真的一个人都没见过你妹妹吗?”
“那条路挺偏的,夏天正午基本没人经过。路边只有三家店,可两家烧烤店是晚上才开门。”
“剩下一家卖茶叶蛋的,是个残疾人,平时扎店里,中午也不开门。所以,没人见过我妹妹。”
老余连连摇头:“这案子真是古怪,简直匪夷所思。”
连他都没头绪,我刚升起的希望又破灭了。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个失踪孩子的照片,和我妹妹一模一样的年龄,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让我心情沉甸甸的。
老余看我神色低落,鼓励我:“小岳,别放弃。尸体没找到,就还有活着的机会。”
“多回忆回忆细节,办案得胆大心细,只要做了什么,总会留痕。回家看看,也许能想起点啥。”
我点点头。
下班时已是深夜,我住的出租房离爸妈家不远,走着走着就到了妹妹当年失踪的那条路……
当年这条路上就两三家小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热闹非常的小吃街。
即便到了凌晨,街上依然有店铺在营业。
老余说得没错,雁过留痕,我肯定漏掉了什么细节。
到底是什么呢?
“茶叶蛋!茶叶蛋!五香茶叶蛋!”
一声吆喝打断了我的思绪。
卖茶叶蛋的王老板闭着眼睛,侧耳听了听,然后对我喊道:“是岳家老大吗?下班了?来来来,来颗刚出锅的茶叶蛋尝尝!”
他姓王,是个盲人,我们那会儿的小朋友都私下叫他“王瞎子”。
他就在这条路边摆摊卖茶叶蛋,已经二十多年了。
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偷偷拿钱去买他煮的茶叶蛋吃。
妈妈不许买,说他是盲人,东西可能不干净,容易生病。
小孩子哪顾得上那么多,好吃才是王道。
大家都说盲人的耳朵特别灵,这话倒没错。
虽然夜深人少,但我周围还有五六个人。
“是我,王伯伯,给我来两颗茶叶蛋。”
小时候买两颗,是妹妹一颗,我一颗。
如今买两颗,纯粹是习惯了。
“好嘞!伯伯还记得你们姐妹俩最爱吃茶叶蛋!”
王伯一边捞着茶叶蛋,一边笑得客气,皱纹像核桃壳那样密密麻麻。
说到后半句,他突然停顿,脸上的笑容也跟着僵住了。
“还没找到吗?那天我出摊晚了,一直待屋里,没帮上忙,真是对不起你了,岳丫头。”
他说这话时还摸了摸鼻子。
这分明是心虚的样子。
“这不怪你。
当年你根本什么都没听到。”
我特意加重了“听”字。
他拿茶叶蛋的手顿时一抖,赶紧拦住正准备扫码付钱的我。
“不用钱!我都听说了,岳丫头你穿上制服了,给咱们老街坊争脸了!这两颗茶叶蛋,伯伯请了!”
“给,拿着,小心烫了。”
王瞎子出了名的抠门,这些年连他亲哥亲嫂子吃个茶叶蛋都得掏钱,今天居然请我吃茶叶蛋?我心里还在嘀咕着,车小心翼翼地接过茶叶蛋,顺手扫了个码。
茶叶蛋两块一个,我转了十块过去。
“支付宝到账十元。”
提示音响起,王瞎子脸色变了,连忙摆手:“丫头,你咋这么不上道,给这么多干啥?”
我凑近他,小声说:“我在查我妹妹失踪案,王伯伯如果有重要线索提供,警局会有赏金。”
他的耳朵微微动了动,愣了一下,长叹道:“你妹妹可真可怜……常金我不图了,我就说说我听到的,真假不敢保证。能帮上忙,以后多来买茶叶蛋就行。”
王瞎子的耳朵非常灵敏,凭听脚步声就能判断谁从他门前经过。
那个下午,也就是我妹妹失踪消息传出来前,有个意想不到的人从他门口走过。
“丫头,多留心,多回忆,身边的人一个都别放过。”
这是他最后对我的叮嘱。
2024年9月25日。
那个失踪的自闭症孩子找到了。
她被海水泡成了巨人观,内脏被海鸟和海鱼掏空,惨不忍睹。
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悲伤得让人心疼。
但哭声震天,听起来却怪怪的。
这大半年,我在警局见过不少离合悲欢。
真正的伤心和痛苦往往无声,甚至流不出一滴眼泪。
可惜,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明这对夫妻是故意将孩子置于险地的证据。
我的心情糟透了。
可能是因为那个受害孩子和我妹妹同岁,
也可能是因为她和我妹妹一样,都有难治的疾病,总能让我想起她。
想起她那一颦一笑,扑进我怀里甜甜地叫“姐姐”,想起她哮喘发作时的无助和痛苦。
我做梦都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她过得好不好?去了哪里?我几乎被折磨得快要发疯了。
2024年10月6日,国庆节的班值完后,我决定去找当年的证人——那个能证明无赖和我奶奶当时不在场的两个人。
老余还说,万一这两人中有人撒谎呢?
只要能撬开他们的嘴,也许真相就能大白,我就能找到妹妹。
我先去了那个无赖的证人张寡妇,又找了我奶奶那边的证人教友周奶奶,花了一整天时间去“调查”她们的说辞。
结果,完全超出我的预料。
2024年10月7日上午9:30,我走进了一个院子。
院子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晾晒着满是盐粒的萝卜条。
看着这些咸萝卜条,我心头一阵揪痛,因为这正是当年害得我妹妹哮喘的罪魁祸首。
我一步步朝老人走过去,回想起当年的事:2005年秋天,我得了肺炎,爸妈带我去市儿童医院治疗,把妹妹托付给她照顾。
那天正好是教友们来家里做礼拜的日子,她忙着招呼客人,根本忘了妹妹。
妹妹饿了跑去找她两次,都被赶了出来。
没办法,妹妹只能吃那满院子晾晒的咸萝卜干。
这些年,每次提起,我的心都像被刀割一样疼,努力控制着眼泪不掉下来,我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傍晚的时候,我们回来时,妹妹已经吃了一整天的咸萝卜干,身边没水喝,一直没喝水。
爸妈急得手忙脚乱,给她催吐,还灌了大量的水,妹妹哭得喘不过气来。
虽然做了补救,但妹妹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她的气道和消化道因高盐损伤,常常吃不下饭,呼吸也困难。
从那以后,她就患上了哮喘。
“你毁了一个本来健康的孩子,难道丝室就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请问,你的主原谅你了吗?”
老人那浑浊的眼睛盯着我说:“做错了事,只要真心悔过,主都会原谅。那个死丫头早就不在了,你翻这些旧账干嘛?”
“如果是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晒什么咸萝卜干!”
我的声音忍不住提高,泪水随着愤怒一同滑落。
老人冷哼一声:“就算她的病是我的错,大丫头,你可是把她弄丢的人,你有什么资格骂我?别以为穿了身警服就了不起!”
我们都渴望伤害我们或我们至亲的人能正视错误,真心道歉。
可现实,往往无情。
“我去找了当年跟你一起做礼拜、为你作证的周奶奶,答应帮她申请减轻处罚,她什么都说了。”
“几十年来,她没睡过安稳觉。我想知道,你呢,奶奶?”
我紧盯着这个趾高气扬的老人,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
她脸色瞬间刷白,手里刚切的萝卜条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沾满了灰尘。
但她很快又恢复镇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陷害我。老周绝不会……”
她猛地咽下未说完的话。
“绝不会什么?绝不会出卖你吗?”
我紧盯着她的眼睛追问。
她的视线飘开,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她猜对了,我的调查并不顺利。
周奶奶确实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她欲言又止,说当年十五年前她在主面前发过誓,证词绝不更改,叫我别再问了。
我不知道我奶奶用了什么手段,把周奶奶哄得守口如瓶。
也许是教规,也许是人情。
那个无赖的证人王寡妇却对我破口大骂,说当年她给那个无赖作证,结果被曝光了开房记录,名声扫地,高攀不了门当户对的人,最后只能嫁给个老光棍,损失惨重。
如今一见警察就心生怨气。
她态度虽糟,但证词倒是挺靠谱的。
所以,也算没白来。
“你不说也没关系,我就是想知道,她……还活着吗?”
我爸妈正好住在奶奶隔壁的院子,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我弟弟正好放国庆假,也凑了过来。
他是在妹妹失踪后的第三年出生的。
那会儿我们市还没有放开二胎政策,为了生他,我爸从一份难得的国企工作辞职,跑去托关系重新办了农村户口。
毕竟夫妻俩都是农村户口,头胎是女儿,才能生第二胎。
这次他们赌对了,生了个男孩。
爸骂骂咧咧地挡到奶奶面前:“刚当上警察就开始伸手指向自己家人了?我和你妈咋就生了个白眼狼呢?”
我冷笑着说:“爸,你难道不想知道妹妹去哪了吗?我就是问问奶奶知不知道,你没必要这么激动吧?她要真没做啥事,查查还能给她洗清冤屈。”
“你敢!”
爸愤怒地举起手。
妈叹口气,十几年来第一次跟我说话:“老大,事情都过去了,妈不怪你了,别查了。你奶老了,受不了折腾。”
她摸了摸弟弟的头,又说:“何况你弟弟以后还得考公务员,你总不能自己考上了,把梯子踢掉吧?”
初秋的阳光照在身上,天气还不算冷,但我却冻得直打哆嗦,冷到骨子里。
今天之前,我刚向老余汇报找了两位证人的情况。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岳,这件案子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把卷宗放回去,算了,安安心心地做好份内的工作。”
“第二,深挖到底,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找到你的妹妹。”
“但代价可能很沉重,不仅会被家族当成异类,家也回不去了,职业生涯也会受到影响。你得好好想清楚。”
可如果我不去查明真相,找不到妹妹,心里的良心难道就不会一辈子难安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用考虑了!如果妹妹还活着,不管她身处何方,我都要把她接回家!如果她没了,不管是谁害死她,都得付出代价!”
以前我一直被自责和愧疚困住,眼界狭隘。
回想起来,只有妹妹失踪前两年,爸妈还忙着满大街贴寻人启事,在网上发布悬赏。
后来,一切就都冷淡下来。
他们让一个孩子背负了所有的罪名,用行动告诉周围的人,这都是我的错。
一家人孤立了我十五年,让我每分每秒都不敢忘记自己的“过错”。
好几次我站在楼顶,眼睛一闭,想一跳了之。
可一想到还没找到妹妹,连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死不了。
万一妹妹还活着呢?等着我去找她呢?或者她是被人害死的,等着我去复仇呢?
十五年了,妹妹,你究竟去哪儿了?
姐姐真的好想你!
我平静地扫了一眼这所谓“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家人,掏出对讲机,“师父,行动!”
院外的警察闯进小院,我奶奶一屁股坐到地上,嘴里嘟囔着:“我明明跟主忏悔过了,跟主悔过了,应该没事的。”
同事带走了暴跳如雷的父亲、咬牙切齿的母亲、颤抖的奶奶,只剩下对我怒目而视的弟弟。
他的个头已经快追上我,拳头紧握。
我走到他面前,语气却温和:“回家吧,你十三岁了,自己能照顾自己了。”
“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你没错,我也没错。你知道吗?你还有一位瘦小可爱的二姐,她消失了整整十五年。我只是想把她找到,带回来而已。”
“也许代价会很大,但我只想给她一个公道。”
“要是有一天你也不见了,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人能一直坚持着把你找回来?”
他头慢慢低了下来,拳头也松开,悄无声息地一步步走出院子,连一句话也没说。
人走了以后,我围着奶奶的院子转了一圈,最终停在一棵树下。
盯着那棵树,眼泪渐渐模糊了视线。
这时,老余打了电话过来:“小岳,你奶奶装晕不配合,父母趁机大闹。没有关键证据,我们会很被动……”
我擦掉眼角的泪水,哽咽着说:“师父,我想我已经找到妹妹了。麻烦您带着法医和两个刑侦科的同事过来一趟。”
挂断电话,我拿起墙角的铁锹,在树下开始一锹一锹地挖着,眼泪一滴滴落进泥土。
上警校时,野外侦查老师曾说过,野外找尸体尤其是有植被的地方,尸体埋藏处周围的草木颜色往往特别深,特别绿。
“尸体其实是很好的肥料,一个成年人身上大约有2.6公斤氨肥。这些氨肥在腐烂过程中会变成铵,也就是常用的氨肥。”
“如果尸体影响了大约3平方米的土地,那么它释放的氮元素,大约是温带树木和灌木氮肥推荐用量的50倍。”
“草木叶片含氨量增加后,叶绿素含量也会提升,所以植物会比周围的同类看起来更绿。”
我记得当时我问老师:“那些其他动物不也能提供氨肥吗?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尸体能让植物有这么明显变化?”
老师回答:“原因有两个。第一,人类尸体腐烂的节奏跟其他动物差别很大。”
“第二,是因为人体内有镉的缘故。”
镉是一种重金属,很容易被植物的根部吸收。
它到达叶片后,会改变叶绿体里一种叫“光系统Ⅱ”的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进而影响叶子的颜色,让这棵树看起来和周围格外不同。
妹妹失踪后,我很少去奶奶家的院子。
上了大学以后,连过年我都不敢回家,于是一直没注意到那棵树。
老余带来了三个壮实的小伙子,脱掉上衣,赤膊开挖。
尸体埋得很深,差不多有两米深。
树根盘根错节,紧紧缠绕着骨头,硬是难以拿出来。
法医小心翼翼地用斧头砍断树根,一块一块地把骨头摆在尸布上。
我戴着橡胶手套,轻轻抚摸着这具瘦小的尸骨,泪水滑落,哭得撕心裂肺。
妹妹失踪的第二年夏天,树下长出了一只甜瓜,长长的藤蔓绕着树干。
我被瓜香吸引过来,发现甜瓜根部竟然有一颗牙齿,样子和妹妹的牙齿一模一样。
我问奶奶,她说是妹妹之前换牙掉的,我当时没多想。
妹妹消失的前一天,刚刚换了第五颗牙,她还托着我帮她把牙齿扔到屋顶上。
你说我当时怎么会那么傻,一点没想到,妹妹失踪当天早上吃了整整一只甜瓜,那棵瓜苗竟然是从她肚子里长出来的。
我痛不欲生,泣不成声。
2024年10月9日,老余的审讯有了重大突破。
经过不懈努力,周奶奶和王瞎子终于同意出庭作证。
面对铁证,我的奶奶和父母全部供认不讳。
当年,你父母是农村户口,政策允许他们生二胎。
没想到二胎生的是你妹妹,一开始,他们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你爸爸为了给家里争取更好的条件,还托关系进了国营企业,拿到了城市户口。
可是,妹妹患了哮喘,病情严重,眼看活不长,他们的想法开始变得不对劲。
当时的政策允许,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户口,家里如果唯一的孩子有残疾或无法治愈的重病,是可以再要孩子的。
于是,一切阴暗的计划就这样开始了。
“所以,实际上你妹妹是被误杀的。他们最初真正想杀的人其实是你。因为只有除掉你,你爸爸才能保住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和城市户口,还能有资格生二胎。”
老余看着我,眼里满是无尽的同情。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心头像被重锤击中,久久说不出话。
“后来你妹妹会被杀,是因为当时那三个人没商量好。你奶奶和你父母约定好了,确定了要除掉哪一个,第二天就让那个人去送饭。”
“那天没人见到你妹妹,是因为她刚出门,就被住在隔壁的奶奶叫住了,给了她一碗‘糖水’。她喝下去后,身体很快就出了问题。”
“你爸在叫醒你前一个小时就回来埋尸了,之后才回家找你。”
“选择午后下手,是因为那个时候太阳最烈,路上没人经过。”
“但他们没想到,虽然王瞎子没开门,却听见你爸的脚步声。”
“他不久后还听到收音机报了13点整的时间。”
“所以,当你爸说发现你妹妹不见是下午两点多时,王瞎子立刻知道他在说谎。”
“当你爸按照约定时间到你奶奶家,才发现自己杀错了人,但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他们会对你有敌意,因为其实计划里,你才是那个该死的孩子。”
“他们提前在树下挖好了坑,把你妹妹埋了进去。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湿土上撒了干土和草屑,还把一群小鸡围在上面,所以没人注意。”
“你妈妈是知道这事的,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合谋演了一场戏,把原本该死的你当成替罪羊,故意误导警方。”
我脸色惨白,手都抖得端不稳老余递来的水杯。
原来,妹妹是替我死的!
原来,那个该死的,是我!
老余叹了口气,接过我手里的杯子。
“案子里还有两个疑点没解开。第一,法医说你妹妹是因为中了三氧化二砷死的,这毒是你爸偷偷从他工作的化工厂带出来的。”
“厂里查得紧,带不出多少,但带出来的剂量足够让小孩子半小时内致命。”
“可问题是,你奶奶描述的情况很怪,你妹妹喝了糖水后,几乎马上就出现呼吸困难,没过五分钟就去世了,那速度快得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个疑点是,杀人这事儿他们都承认了,但没人承认往你杯子里下过安眠药或者催眠药。”
“你妈说她那阵子睡眠不好,买过安眠药,但坚决不认是她给你下的。”
“而且你家那个仇人都有好几个不在场证明,他也不可能是凶手。”
“我现在在想,或许我们之前的推断有误,根本就没安眠药这回事。也许,那天你只是轻微中暑了?”
我坚定地摇头,嘴唇微微颤抖:“不,师父,绝不是中暑。你的判断没错。谁下的药,我大概知道了。”
现在,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之一,申请高级催眠师对我进行催眠,试图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感觉一定还有什么细节是我没注意到或者忘记了。
2024年10月10日14:00。
催眠师开始对我实施催眠,下面是催眠的主要过程。
催眠师问:“现在你回到了2009年8月10日中午11点30分。你和妹妹都在家里,那时你们在做什么?”
我回答:“在做饭。”
催眠师继续问:“天气热吗?”
我说:“热极了,汗都湿透了。”
催眠师追问:“你喝了很多水吗?是自己去喝,还是有人递给你?”
我答道:“喝了很多水,没时间自己去倒水,都是妹妹递给我的。”
催眠师问:“水看起来和闻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像水里带点粉末,味道怪怪的。”
催眠师又问:“那时家里还有别人吗?”
我回答:“没有,只有我们俩。”
催眠师继续:“做完饭后,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很累,四肢酸软,犯困,头有点重。”
催眠师问:“妹妹那天的状态怎么样?”
我答:“特别粘人,死抱着我不放手。”
催眠师说:“现在仔细回忆一下,妹妹送饭离开前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
我想了想:“她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没有笑,反倒有点想哭。挎着篮子准备走的时候,顺手从廊下掏了一把东西揣进了口袋。”
催眠师追问:“廊下有什么?仔细回忆一下。”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是去年晾晒的咸萝卜干。”
话刚说完,我就控制不住地浑身抽搐起来,这明显是情绪波动导致的反应。
催眠师连忙结束催眠,迅速把我唤醒。
他说:“你妹妹因为咸萝卜干腐蚀了气道,对它特别严重过敏。医生也再三叮嘱过,如果再吃萝卜干,那就得准备后事了。”
他说到这里,眼里泛起了泪光,“所以……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救你。”
我哽咽着说不下去。
老余接着说:“安眠药其实也是她给你下的,目的是替你去送饭。”
“为了确保自己一定活不过去,她出门前还特意吃了一根咸萝卜干。”
“就是因为这样,喝了你奶奶递过来的‘糖水’后,她才会那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个才八岁的孩子啊!小岳,你妹妹是真的很爱你的。”
“那些年,她一直被病痛折磨,心里变得敏感又多疑。”
“她总是偷偷听大人的话,知道自己成了这个家的负担,也察觉到大人们的冷漠和无情,所以,才会这样……”
我的心像被一万根针扎透一样,血一点点地渗出来,但眼泪却怎么也流不出来。
老余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岳,好好活下去。这是你妹妹最后送给姐姐的祝福。你的命是两人份儿的,特别珍贵。”
案卷交到法院后,父母要求见我一面。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去了。
“岳夏,你毁了我们的家。”
爸爸冷冷地盯着我,“你为了那个丫头,断送了我和你妈的晚年幸福,更害了你弟弟的前途。”
他眼神里满是敌意,就像我成了他的仇人。
妈妈也满是怨恨,“要不是你死抓不放,谁会在意那个病秧子,那个丫头的死活啊?”
“那年,死的要是你该多好。”
我红着眼,声音哽咽:“对,我宁愿那年死的是我,把活下来的机会留给妹妹。”
她那么懂事,那么可爱,才不过八岁。
“你们根本不在乎她,我在乎!只有我们彼此关心彼此。”
“现在,把你们送上法庭,送进监狱,我心里可是痛快极了!”
话一落,我嘴角轻轻上扬,露出一丝笑容。
那笑,却苦涩至极。
“你们这两个讨债鬼,赔钱货!你们俩的命加起来都比不上我儿子一个的价值!”
“你懂什么?农村里没有儿子的人,会被人当成笑话,背后遭人指指点点,受尽欺负和轻视!我们这样做难道错了吗?”
观念完全不同的人,永远无法好好交流。
我摇了摇头,站起身,冷冷地对他们说:“祝你们服刑愉快。”
转身离开。
后来,我将妹妹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她的坟上种满了她最爱的雏菊。
每个周末,我都会带上一碗自己亲手煮的面条,放在她的坟前,跟她说说话。
“妹妹,别害怕,姐姐会一直陪着你。如果有来世,我们做一对双胞胎姐妹吧。”
“那时,一定会有一对爱我们的父母。”


全华班也能进3球, 国安保持4后卫别折腾了, 张玉宁打开心结


现代石英钟表推荐哪款?这5款高颜值又耐用!


两千年前的“基建奇迹”,至今还在吊打现代工程?


回顾∶红军最特殊最悲壮的部队:少共国际师之少年有志报神州


常州武进球场悬空顶棚材质如何挑选


瞩目!杨振宁追悼会上,93岁弟弟杨振汉现身,透露哥哥一个遗憾